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经历了西学的两次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化自信,但在西强东弱的竞争格局中不得不接受全盘西化论的冲击;革命文化促成了救亡图存的伟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促成文化自信的复兴。为什么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欧风美雨的西学冲击持续已然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又需要在文化复兴的努力中总结哪些经验教训?这都是我们在讨论文化自信时必须加以解析的逻辑和历史问题。
文化自信与中国传统文化
近代以前,中国人有着延续数千年的文化自信,伴随华夏中心意识的不断强化,以文明与野蛮区分夏、夷的天朝上国观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际。自然,这种文化自信有其国威远布、剿抚蛮夷的现实来源。但我们还需关注中国传统的观念结构,藉以理解这种文化自信的思想来源,以及这种文化自信为何会在近代面临危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哲学与自然哲学不可分离,“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精辟地概括了其观念结构。与基督教在天地与人之外引入上帝作为二者共同的造物主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天地生人的观念。《易·序卦传》中“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的看法,在将自然万物看作人的前提的同时,也预告了结合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的思维路径。如果说“道”是自然运行的外在规律,那么“德”就是人生安顿的内在法则,而且需要追求二者结合不露痕迹、浑然天成的理想状态。在老子看来,一定是《道经》《德经》合则俱成,分则共灭,也只有不显示出造作形式的“德”才是真正的有“道”之德,而努力维护道德外在形式的“德”却不是真正的有“道”之德了。因此之故,我们才把他的经典之作称为《道德经》,才能在里面读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在这样的观念结构中,将个人价值的立足点放在“道”上,强调“人能弘道”,提倡《论语》中所说“君子忧道不忧贫”,是符合逻辑的。这一体系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是个体生命暂时性和天地万物永恒性之间的矛盾。最自然的方法是将个人安置在家族和社会之中,以个体的不断更新来保持血缘和族群的生生不息,从而实现“道—德”结构的圆满。这样,自然哲学与人生哲学完满地合二为一,并发展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结论来。这种精神结构对“道”的终极追求,在普通百姓那里人格化为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天地为本,君师行道,亲则为始,都是“道”的本源和表现;在读书人那里则表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人生理想。传统中国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得以安放,而“吾道一以贯之”,为此不惜杀身成仁的文化自信也由此建立。
传统文化自信的观念结构,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形式上的统一性和追求上的超越性。在形式上,这种观念结构拒绝承认其“道”会随时空不同而变化,而是强调《荀子·解蔽》中所讲的“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在内容上,这种观念结构所要求的精神归宿并非指向边沁式的个人收益,而是超越个人算计的道义。孔子在《论语·阳货》讲的“君子义以为上”,将个人有限价值放到天地生民的无限之“道”中进行考量。至于具体的做法,即“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操作路径,只是将个人有限价值放大为天地生民的无限以求“道”的不同选择罢了。当功利与道义矛盾时,君子自然要安贫乐道,甚至可以放弃生命。
传统文化自信的这两个特点,对近代中国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种在个人层面上重义轻利,在国家层面上重“王道”轻“霸道”的文化自信,妨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无助于改变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空间扩张过程中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另一方面,“道一无二”的形式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拒变恐化,又让它在西学的冲击下显得不够灵活。“中体西用”的主张为求适应时势,强行切割了体用一致的文化逻辑,但显然有悖于“吾道一以贯之”的传统思维形式,终究未能持久。西方中心主义者反倒是为了保留“天下无二道”的传统思维形式,而把“道”的内容替换为欧美模式的全盘西化,绵延百年而其音不绝。这种主张当然会造成传统文化自信的急剧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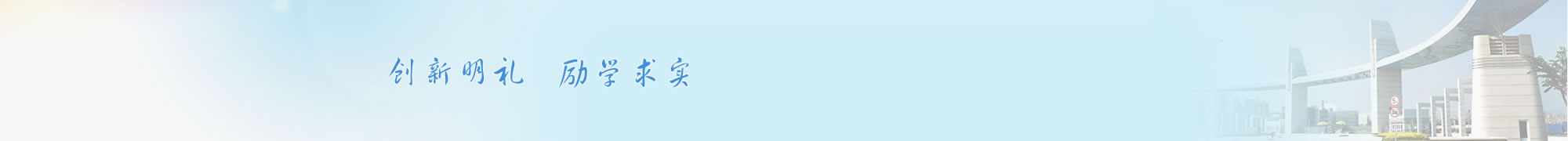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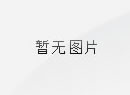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51110202002224号
川公网安备51110202002224号